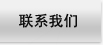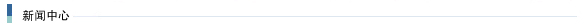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路艷霞 發表時間:2014-07-03
“今日頭條”新聞客戶端版權事件引發了傳統媒體的集體聲討和社會熱議,傳統媒體與新興網絡媒體的矛盾和紛爭再次爆發。
在眾聲喧嘩中,一個聲音顯得愈發清晰:隨著移動新媒體的不斷成長,長久以來傳統媒體的版權之爭再次凸顯。在傳統媒體面臨轉型的時候,在新媒體不斷涌現的時候,解決傳統媒體的版權困局,比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版權價格有變,合作模式沒變
在北京晚報資深編輯沈灃的記憶庫里,封存著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距今已有十幾年了。
1998年,北京晚報副刊和初創不久的新浪網山野論壇有過合作,沈灃因此結識了一個叫陳彤的年輕人,他每次來時總背著一個單挎包。陳彤人很熱情,編輯部電腦壞了,一個電話打過去,他就會趕過來幫著修理。讓沈灃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小伙子后來也會和新聞打交道,如今已是新浪網執行副總裁。
沈灃其實是見證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多年前,在一次聚餐中,陳彤告訴他的一幫哥們兒,新浪網要做大的新聞平臺,五秒鐘更新一次,而沈灃心里嘀咕的是,“新浪沒有記者,內容怎么能五秒鐘更新一次呢。”后來,沈灃才發現,新浪刊載的新聞原來都是用報社、通訊社的稿子。
事實上,新浪網正是在1998年正式涉足新聞領域,成為國內第一家推出新聞業務的門戶網站。新浪網副總編聞進回憶說,新浪網新聞頻道的萌芽始于1998年汪延(原新浪網總裁)從法國世界杯發回的首輪報道,此后才開啟了新浪與新聞的交集。而這個新興事業之所以能延續下去,更重要的是因為新浪聚合了一群對新聞充滿了熱愛的人。
北京晚報成為和新浪合作的首家媒體,聞進說:“和北京晚報合作的時候,雙方都不知道怎么簽約。后來,對方做出了一個決定:在雙方確立有償合作的前提下,內容使用和簽合同同步進行。” 但據了解,那個合同并沒有涉及版權費用問題。
新浪不斷展開的媒體簽約大戰,至今仍令聞進印象深刻。一開始,媒體并不了解新浪在做什么,也認為其規模很小,即使合作也不可能帶來顯著收益效果,“但媒體天生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及友好的態度,讓他們從一開始就嘗試著與我們開始合作。”聞進說,至今對每一個在最初以開放冒險和包容心態,向新浪打開合作之門的媒體充滿敬意。
起初,國內幾乎沒有傳統媒體通過與網站合作獲得版權收益。但聞進回憶,人民日報是個例外,“人民日報是繼北京晚報之后的第二家與新浪合作的媒體,我們兩家一開始就有版權交易,盡管當時我們付的錢很少。”
漸漸地,和新媒體合作的尷尬局面,讓傳統媒體開始心有不甘。2005年11月,全國二十多位都市報老總在南京聯合起草并發布了一份《南京宣言》,發出了“不再容忍商業網站無償使用報紙新聞產品”的呼聲。
宣言的聚合效果,至今令人質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聞進還是感到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2006年7月國家出臺《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之后,版權價格開始發生了驟變。“2007年的時候,版權價格就上升了,新華社稿件版權價格上升了數百倍,一般媒體有十倍、幾倍的。總的來說,2007年時的版權費用是2006年的近兩倍。”
聞進說,就新浪而言,版權合作從一開始就是正規的簽約授權,如果沒有現金投入,也會有很多的資源置換,比如宣傳廣告置換等等。如今,新浪與傳統媒體的版權合作資金支出是一筆不小的數字,“我們目前和國內外八九百家媒體合作,與鼎盛時期的2300家媒體相比,已有所減少。”據報業人士分析,數量減少有一個原因,就是雙方沒有談妥合作條件,因此放棄了簽約。
盡管價格在變,但不變的是新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采取的內容打包的合作模式。至于版權價格,報業資深人士透露,各家不盡相同,有的價格高,有的價格很低,有的甚至是免費。由于沒有找到更好的合作機制,這樣的模式從上世紀9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了現在,沒有過改變。
生產成本和版權收益嚴重不對等
“如果人人都是拿來主義,就沒有人再愿意去做原創了。”——新京報傳媒副總裁劉炳路。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合作,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等大的門戶網站都建立了內容授權機制,每年都會支付很大的費用給傳統媒體,但是一些小網站,不加授權使用的情況卻很常見。”騰訊互聯網與社會研究院副秘書長張欽坤說。
面對復雜的版權環境,傳統媒體的抱怨聲越來越多,內容生產成本和版權收益嚴重不對等是最大的焦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報業人士訴苦說,“2010年開全國‘兩會’,報社派出了20人的采訪組奔赴北京,統計住宿、交通、餐費等成本,算下來平均每人1萬元。如果再把工資、獎金算進去,這20人的支出至少要27萬元至30萬元。”但凝結著記者、編輯心血的“兩會”報道,一夜之間就被一些網絡媒體轉載,而這些網站沒有打任何招呼,更沒有支付任何稿酬。
關于傳統媒體與網站的版權合作現狀,很難有一系列準確數字來概括,但據資深報業人士透露,比較有實力的媒體從一家網站獲得的版權收益,每年大約為20萬元至30萬元;像新京報這類媒體,每年版權收益大約為幾百萬元,在傳統媒體中已屬翹楚。
但新京報傳媒副總裁劉炳路顯然對自家版權收益并不滿意,“不計印刷、紙張費,每個字成本都有5塊錢,而打包賣給網站的版權核到單篇稿子、單個字的話,估計連一分錢都沒有。”他坦言,相對于其他的媒體,新京報的版權收入還算比較多的,有更多的傳統媒體連錢都不要,讓一些網站去白白使用。
除了版權收益低之外,不給作者署名、不標明出處、斷章取義、掐頭去尾等情況也很常見。東方早報資深記者石劍峰說,他采寫的有些報道經網絡轉載后,經常不給他署名,也未標明來源,而且一些網絡媒體常常會在長度上做些刪減,標題也會有改動,文章的意思有時就發生了改變。
更讓傳統媒體無法忍受的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興起,其版權遭到肆意侵害的情況更為普遍。據重慶日報報業集團法律事務部副主任邱敏觀察,電腦屏幕因為面積較大,一般來說,作者、鏈接、出處還能展示出來,“但手機就有局限了,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報紙內容的精華會被直接抓取過去。而來源、作者、鏈接等等,全部都減省了。”他認為,這也讓傳統媒體的版權維護遭遇更大的困境。
“如果人人都是拿來主義,就沒有人再愿意去做原創了。”劉炳路對此深感憂慮,他認為侵權的泛濫會加速新聞作品質量的下滑,會重創原創精神,“如果沒有人再愿意去扎扎實實地做采訪,網媒也同樣失去了優秀作品的來源,光靠搞笑段子、論壇發帖、整合歸納、互抄互轉,就失去了內容根基。”
賠償標準低,侵權者沒壓力
“法院參照的規定,對文字作品非法轉載的賠償標準是千字50元。”——北京潤文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巖
盡管遭遇種種版權困境,但長期以來,堅持通過法律訴訟或者協會組織解決糾紛的媒體并不多。
張欽坤以前在中國版權保護中心任職,他就明顯感到,傳統媒體的訴訟案例少見,報社發出律師函也少有。相比之下,視頻、音樂、動漫等行業,往往會積極維權。“可能大家認為一篇稿子值不了多少錢,訴訟標的少,所以不愿意輕易走法律程序。”張欽坤分析說。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也坦言,“傳統媒體對我們無所謂,沒有幾家愿意和我們合作。”在他的印象中,只有新京報、南方周末在遇到問題時,曾與文著協進行過溝通。
如張洪波所言,在很多業內人士眼中,新京報是少有的維護自家版權很堅決的媒體之一。新京報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2005年,我們發現,很多門戶網站都沒有獲得相應的授權許可,就任意刊載新京報的稿件。為此,我們采取了大面積的維權行動。”新京報首先與全體采編人員簽署了版權歸屬協議,明確所有職務作品的版權屬于報社。并向侵權網站發律師函,促成合作溝通。“此次維權行動引起了業內人士的關注,也促成了新京報與多家網站的合作,但此間付出的溝通成本非常巨大。”這位負責人稱。
新京報的維權之路并不容易。這位負責人說,2006年,我們起訴TOM網站,被稱為 “傳統紙媒訴新媒體第一案”,當時曾被人罵“想錢想瘋了”;2007年,起訴浙江在線,遭遇了各種阻力,歷經三年的拉鋸式訴訟,最終和解結案;2011年,起訴iPad新聞類免費應用軟件“中文報刊”的開發者邁思奇公司,被稱為國內首起針對iPad應用的版權訴訟,歷時近一年,僅獲賠10萬元。“在將近十年的維權歷程里,我們一直呼吁各界關注互聯網內容轉載中存在巨大的知識產權黑洞,但直到今天,居然還有很多人認為新聞是不受知識產權保護的。”這位負責人非常不解地說。
這位負責人認為,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變化,傳統媒體維權的對象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門戶網站到移動終端,從APP到微信,在網絡時代,新媒體攫取新聞產品的速度越來越快,技術手段越來越成熟,利用法律空隙的方式也越來越多,“但我們的維權依據、標準、方式和外部環境都沒有太大的變化,這也是很多傳統媒體無法堅持維權的主要原因之一。”
對此,北京潤文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巖表示認同。他仔細分析道,首先取證難就是一個大問題。張巖舉例說,“網站侵權進行取證,就要進行批量公證,30頁以內公證費是800元至1000元,如果超過30頁還要再加錢,每頁50元、100元、200元的都有。”張巖說,為了取證,少說要公證幾百篇、上千篇稿件,甚至幾萬篇稿件,“因此,公證費用前期最便宜的也要花掉一兩萬元。”
由于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取證在如今變得更加困難,張巖認為,如果微信公眾號、自媒體發生侵權,等你發現時,往往難以固定證據。
賠償標準低也令媒體很難下決心打官司。張巖說,“國內絕大部分法院參照的都是1999年國家版權局頒布的《出版文字作品報酬規定》,對文字作品非法轉載的賠償標準是千字50元,即便賠償標準高的,最高也就達到50元的2倍至5倍。”更令他不解的是,目前還沒有一家法院提出,這個賠償標準應該隨著中國國家物價指數的變化予以調整。
“用一篇文章不就賠償兩三百塊錢嘛,加上律師費也就一兩萬元,一些侵權者常常會說,這對我而言沒什么。”張巖由此感嘆,賠償標準低,侵權者沒壓力,侵權行為變得更加隨意了。
“為了維護權利人的權益,保護知識產權,這些司法實踐中的難題,應該引起重視。”張巖呼吁道。
建立共贏機制才是正道
“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能否建立一個合作規則?”——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
靜觀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矛盾和多次交鋒,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總干事張洪波總結道,兩者之間的矛盾總會在新媒體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在一定的節點爆發,《南京宣言》也好,“今日頭條”事件也好,都是遵循著同樣規律。
面對多年來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禾有一個強烈印象:傳統媒體總是在訴苦,聲稱別人在市場掙了錢,卻常常忘記自己是否需要創造新機制出來,以解決不斷出現的問題。“傳統媒體手上有那么好的資源,卻沒有很好地利用,沒覺得自己是市場主體,少有采取市場化的做法,對此,我很遺憾。”
張洪波也表示,傳統媒體在面對新媒體所帶來的機遇或挑戰時,版權意識確實還很淡薄。“缺乏對新聞作品作為版權資產進行科學、有效、合法管理和維護的能力,當慣了官方媒體,自以為有意識形態的尚方寶劍和國家保護,從沒有看上自身的版權資源和版權資產的發展后勁兒,更不了解著作權行政保護這一行政救濟措施。”張洪波直言。
文著協曾走訪了十幾家傳統媒體,關于媒體和記者職務作品版權歸屬問題,這些媒體大都沒有統一的規定。張洪波說,他們曾建議按照現有的法律規定,記者入職時,應該和媒體簽訂一個版權協議,或者在勞動合同中加入具體條款,明確職務作品版權歸屬,“比如在本報本刊發表作品之日起,版權歸報社,兩年之后,版權歸記者。報刊社對網絡新媒體授權獲得的收益,應當與編輯記者進行利益分割。”但目前絕大部分傳統媒體都沒有和記者簽訂類似合同,很多編輯記者都不知道,自己在職期間創作的新聞作品版權到底歸誰。“如果是這樣,傳統媒體遇到侵權時進行訴訟,代表編輯記者維權,就變得非常困難。”張洪波說。
文著協還對傳統媒體的版權聲明進行了調查,情況并不樂觀。在國家圖書館拍攝了上千份聲明之后,文著協進行了仔細分析,“大部分版權聲明都屬于科技期刊、學術期刊,但大多不符合法律規定,不僅沒有在顯著位置長期公示,而且很多期刊所聲明的紙介質稿費包含電子版稿費都是一紙空文——根本就是原來紙介質的稿費,沒有因為電子版做任何調整。”張洪波說。
“是大家聯合起來維權,還是自己單槍匹馬地去法院起訴,這是每個權利人和每個媒體自己的選擇。”但張洪波認為,在目前紛亂的版權環境下,尤其對于那些勢單力薄的傳統媒體和名不見經傳的普通編輯記者來說,集體維權或許是更好的選擇。
他透露,文著協正和有關部門、有關行業協會進行溝通,幫助傳統媒體規范版權聲明,愿意促成傳統媒體和新媒體之間建立全新的合作機制,“按照《著作權法》和實施條例的規定,單純事實消息不受法律保護,政治、經濟、宗教等時事新聞屬于合理使用,除此以外,其他新聞作品都受法律保護。基于此,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能否建立一個合作規則?”張洪波設想,按照這個規則,傳統媒體和作者可將每次發表的新聞作品主動分類,在幾方建立并認可的平臺上進行作品備案、公示,標明新聞作品的作者、來源,標明轉載作品不得進行刪改,制定網絡付酬標準,并規定網絡媒體付酬的具體期限以及罰則等。
此外,張洪波認為,創新授權機制也值得探討, “比如我們應該商討,傳統媒體除了正常版權收益之外,是否還要關注到新媒體由新聞作品、單純的事實消息等所帶來的流量,以及其產生的廣告收益,并進而商討廣告的分成問題。”
雖說傳統媒體維權狀況堪憂,但西南科技大學新聞系主任劉海明還是捕捉到一些全新的變化。他注意到,廣州一些報紙采取電子版下午上網的做法,以保證其報紙上午零售的正常進行。《人民日報》采取電子報“付費墻”的做法,第一天的報紙可以免費在線閱讀,從第二天起讀者就需要付費閱讀。還有的報紙在頭版下面刊載版權聲明,以告誡讀者尊重其版權等。傳統媒體做出的維權動作,也讓人們看到這個行業充滿希望的亮色。
編輯:北京潤文